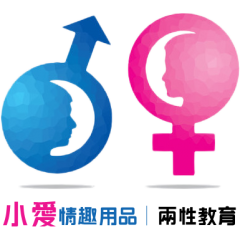人都慣用“純情”二字來形容漂亮的女孩子,但殊不知男孩也有很純情的。我暫且自以為一個吧。說來難以讓人相信,二十六歲的我至今未正式交過朋友。
並非我有什麼缺陷,而是我始終不渝的相信會有一位女孩子真心地等著我;好像胡適文章中的一句話:“我將在茫茫人海中,尋找我人生之唯一伴侶,得之,我幸,不得,我命。如此而已。”
真的是如此而已了嗎?其實,在我懵懂異性的時候,也曾暗戀過一位女孩,那陣兒,我才上中學,班上有一位身材嬌小,相貌可愛的小女孩讓我心動。
可惜。她已經談朋友了,且那人高大威猛,惡名在外。我自忖孱弱無力,很有些不敢造次的;然而讓我不敢造次的還不限於此,即使在她與朋友分手了。
她也會立即選擇上班上高大俊美的男生,況且,終在不停地像換衣服一樣簡簡單單,而看不出半點拖泥帶水的痕跡;我無隙可乘,當然也有些自慚形穢。
我們在校很少說話,好像是兩個圈子裡的人,又由於我的性子,根本不可能接近她(後來才聽她說也不敢接近我,因為她認為我屬於那些學習較好的人)——
然而有一天她主動用電話和我聯繫了。我知道在這個班上只有我們兩人家里安了電話(因為父母親是乾部)。當時很少人家能有電話,所以,父親辦公用的電話我是很少碰的,不是不想,而是無人可通話。
她主動和我通話大概是出於好奇心,而對於我到是樂於接受,畢竟找到了與她接近的方式了。一時間,我得到了兩種樂趣——對打電話的樂趣以及和她談話的樂趣。
電話中我們什麼都覺得好聊,甚至還唱歌給對方聽,或者放一盤好聽的音樂。我們相互打電話問功課,問時間,問天氣,問一切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事。
不見面的談話的確能給人充分思考的時間,以及毫無窘態的莫名的樂趣。那陣兒,我們誰也不願輕易擱下電話的,即便有事,也說一聲——等著,做完了又來打。
我知道她僅是處於對電話本身的興趣,對於我本人,她根本是無所謂的,她根本不在乎電話對方站的是誰,誰對她來說都無所謂的,她只愛打電話,僅此而已。
於是,我們電話裡有說有笑,學校裡依舊行如路人。
她依然有排著隊的男朋友,而我依舊只能在遠處默默地看她——
年華易逝,轉眼快畢業了,畢業那陣都很忙,忙得連告別都不必說。我想,她大概永遠不會給我來電話了;於是,我悄然拿了一張放在老師桌上的她的畢業寸照。那隻是為了多年以後能想起她而做的冒險。
然而,這時候,她來電話了,說有人看見我拿了她的相片,叫我趕快還給她,她還要辦證用。我記得我當時很慌,手裡拿著相片,嘴裡卻在一個勁地否認。
後來,她掛了,我的心還在砰砰跳不停。我想彌補這個過失,卻又不肯就這麼放棄相片,於是,我拿出畫筆匆忙臨摹下來,便一口氣跑回學校,將相片放回了原處,希望老師發現後,能及時地還給她才好。做完這一切,我才心有餘悸地回到家——
又一個轉瞬之間,我從一名無憂無慮,總以為時間是漫長的小男孩,長成了一位過一年就像過一天一樣簡單的小伙子的時候,我才發現我已經換成了時間的快車,而這趟車上,不管我願不願意,我再也回不到過去的驛站,我只能向前,並且無心留戀風景,腦海裡總也是一片空白。
對年齡的恐慌,使人寂寞,使人無奈。朋友也各行其是,他們大多帶著孩子像完成歷史使命一樣,掛著幸福安逸的笑容,在街上消耗著年輕的生命——而我呢。
雖然不願苟同於此,但不免會生出許多羨慕來。也許,在這太平的日子,能得到一個女人的心,有一個幸福的小家,或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呢。
“我將在茫茫人海中尋找我人生之唯一伴侶,——然而,她又在哪兒?
去年,我在單位裡碰見了兒時的她。她是臨時藉調來這兒的。我並未感到興奮,因為我已經將她作為一種兒時記憶的片段放在了心裡最深的地方,就彷佛是一杯隔夜的茶水,茶葉深深地在杯底,茶水雖濃,卻無一絲兒醉人的香氣了。以後見面多了,僅僅以成年人方式打個招呼。——但是,有一次卻讓人覺得有些異樣了。
那是在食堂裡,她老遠跑來管我借碗用,說是要打點湯喝,我只好藉給她,可是到我吃完飯以後,我發現她依然沒有碰過那碗湯,我就上前問,如果不想喝了就到了,我準備走了;她說,她還要喝呢,說著,便猛喝了一口給我看。
我只好說,不急,我先上班去了,回頭到單位來還我就成。她很高興地點點頭。那以後,她老是有意無意地出現在我面前,我覺得她一定在做一件深不可測的事情——
終於有一天接到她的一位女友的電話,說起了她,我並不驚訝,但是也不知該如何回答,我突然間發現久已企盼的事發生後,心卻像死水一樣平靜,我找不到一點當初的感覺,或是說並不能很快地接受。
我不能接受她的原因有很多,其中最主要的還是懷疑她的誠意。
以後的日子,睡眠的多半為了揣摩她而被佔用了。我擔心她僅僅是出於年齡的增長,而急於找個避風的小港,或是心裡暫時的孤獨,找個人依托——
但是,如果她是有誠意的,我又怎能忽視她的感情呢?
這一夜我失眠了。那久已深睡的茶葉,被她輕易地翻弄得直旋而上,在思緒中不停懸浮。我決定了,打個電話給她。
第二天,她的女友恰好來了電話,問我可否帶她到我家去玩。她女友很熱心,我同意了。當天晚上,我接待了她們,一起聊得很開心。
確切的說,是她女友聊得很開心,她佔用了談話的多半時間;也好,這便少了我們許多的尷尬。她那天很沉靜,象十八歲以前一樣面色微紅,只是用眼睛在不停說著,掩不住內心的喜悅。
我盡量使自己的言辭詼諧,但往往出現尷尬的場面,不過還好,不管聽到任何話,她都是在微笑不語,並且,最終是帶著這種表情離開的。
這以後,我開始主動約她,偶爾能打電話找到她,便出去散散步。我將兒時戀她的情節說了,開始她並不相信,以為我是在做戲,當我將那張小畫給她時,她才不得不承認這是真的了;
我告訴她,明天正好生日,希望她能來。她開心地問我需要什麼樣的禮物。我說,找個禮品帶系在你腰上,你就是我最好的禮物。她會心的笑了。
然而,生日那天她沒來,我失望,打電話找她,她說家裡有客人,晚些來,我很沒趣兒,直等到夜裡十二點鐘,沒有她的音訊。